关于服饰的唐宋诗句(有关服饰文化的唐诗及诗句对服饰的解释)
1.有关服饰文化的唐诗及诗句对服饰的解释
记得白居易曾有《缭绫》篇,说“缭绫缭绫何所似?不似罗绡与纨绮”,那么像什么呢?“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,四十五尺瀑布泉”。
要何等的形象思维能力,才能写出如此的意境?!诗人看到的织物上,“中有文章又奇绝,地铺白烟花簇雪”,而且是“织为云外秋雁行,染作江南春水色”。 再细看,“异彩奇文相隐映,转侧看花花不定”。
多么美的天地奇景!哪里是什么缭绫,分明是作者眼中心中的大自然。写诗的人由此及彼,也说明织丝的人不仅有绝技,同时有着活跃的艺术细胞,更有着对大自然的深深的爱。
不然的话,怎么会引起诗人浮想联翩,以至文思如泉涌呢? 白居易还有一篇《红线毯》,说的是用丝织成的地毯。 “择茧缫丝清水煮,拣丝练线红蓝染”,分明是工艺过程。
“染为红线红于蓝,织作披香殿上毯”,是说的红蓝花染成的丝线,比红蓝花还红。这种夏季开出红黄色小花,可以制胭脂和红色颜料的植物,因“其叶似蓝”而被称为红蓝花,这在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二十“诂笺”中有云。
浅毯多大呢?“披香殿广十丈余,红线织成可殿铺”。红毯多美呢?“彩丝茸茸香拂拂,线软花虚不胜物;美人蹋上歌舞来,罗袜绣鞋随步没”,多么形象!诗人认为在丝的面前,其它质料都无法与之相比,“太原毯涩毳缕硬,蜀都褥薄锦花冷,不如此毯温且柔,年年十月来宣州”。
悠悠唐诗,寄寓着诗人对艺术的独特视角与见解;靓靓唐丝,记录下那一个年代人对艺术的深挚的追求与探寻。时至今日,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何尝只是美? 。
2.中国古诗中描写服饰的有哪些
“群山万壑赴荆门,生长明妃尚有村。一去紫台连朔漠,独留青冢向黄昏。画图省识春风面,环空归月夜魂。千载琵琶作胡语,分明怨恨曲中论。”(杜甫《咏怀古迹》)
西施咏
艳色天下重,西施宁久微。
朝为越溪女,暮作吴宫妃。
贱日岂殊众,贵来方悟稀。
邀人傅脂粉,不自著罗衣。
君宠益娇态,君怜无是非。
当时浣纱伴,莫得同车归。
持谢邻家子,效颦安可希!
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
其一
云想衣裳花想容
春风拂槛露华浓
若非群玉山头见
会向瑶台月下逢
这是的第一首,描写贵妃花儿般的容貌和仙子般的体态,这个大家都没异议。但有一个问题,“云想衣裳”的云是什么云?——是乌云?是火云?还是彩云?我想,当是白云。你看后面两句“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”,这岂不正是白色的的感觉吗?所以,当时贵妃是穿着白色的衣裳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吧。
其二
一枝红艳露凝香
云雨巫山枉断肠
借问汉宫谁得似
可怜飞燕倚新妆
我觉得这首是写牡丹。
“一枝红艳露凝香”——正是花之形貌。
“云雨巫山枉断肠”——乃谓花如有灵,即使当年巫山之云雨亦不堪相比。巫山云雨乃自然现象,而牡丹花亦是自然景观,不正好可以相比吗?倘若云雨有神,则名花更当有灵。昔日楚襄王“断肠”于巫山云雨之美,却不知如今牡丹之美更胜一筹。
“借问汉宫谁得似,可怜飞燕倚新妆”——“汉宫”代指唐宫,“飞燕”代指贵妃,唐宫佳丽三千,有谁可比牡丹之美?唯有贵妃而已。
其三
名花倾国两相欢
常得君王带笑看
解释春风无限恨
沉香亭北倚阑干
这首写君王。倾国之美人与绝世之名花“互相欣赏”着,君王则在一边带笑而看之。牡丹花开已是暮春时节,百花纷纷凋谢,春风岂能无恨?而此时此刻,复何恨之有?
总之,第一首写人,第二首写花,第三首写君王。写人之美,则用花来形容——“春风拂槛露华浓”。写花之美,则用人来比衬——“可怜飞燕倚新妆”。美人对此名花,自是欢喜不禁。却不知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乐坏了旁边的君王。
3.请问有没有形容隋唐时期服饰的诗句或简单的介绍
隋唐时期的服饰文化 衣:基本是华夏衣冠、魏晋旧制的损益。
据《旧唐书,舆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载,天子冠服十四种:大裘冕、衮冕、(敝鸟)冕、毳冕、绣冕、玄冕、通天冠、缁布冠、武弁、弁服、黑介帻、白纱帽、平巾帻、白(巾合)。 其形制及冠戴的时期详于两《唐书》。
与前期不同之点是各种冠冕巾帻,天子在不同情况之下都要戴;另一方面,各种冠冕除大裘冕外,臣下也能分别冠戴。即一品戴衮冕,二品戴(敝鸟)冕,三品戴襄冕,四品戴绣冕,五品戴玄冕,文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,从祀时皆戴一种绸制的爵弁。
武弁,武官朝参时或在陛下作武舞者服之。弁服,文官九品办公事时服之。
衣裳的花纹、颜色,以天子服衮冕时,亦即践祚、饷庙、征还、遣将、钦至、加元服、纳后、元日受朝贺、临轩册拜王公等大典时为例:是青色衣、纁裳。画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、火、宗彝等八章在衣,绣藻、粉米、黼、黻四章在裳,共为十二章。
这就是俗所谓龙袍法定样式。 群臣的章服也是青衣纁裳。
以门下侍中、中书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宰辅贵臣为例:共具五章,衣上画宗彝、藻、粉米三章,裳上绣黼、黻二章,外加紫绶,金银缕(般革)囊、金饰剑、水苍玉佩、朱袜、赤晨。官阶大小完全以章之多少及佩饰为区别。
以章而论:一品九章,二品七章,三品五章,四品三章,五品一章,即所谓“章服”。五品以下就不再有章。
所戴的弁服,皮制,通用乌纱。所以有乌纱帽之说。
正式章服以外的常服,从隋文帝开始,穿赭黄文绣袍,乌纱帽,六合靴,和贵臣通服之,只天子带上有十二个环,以资区别。 唐代则经过多次改变,最后规定三品上服紫,金玉带十三(钅夸)(带上的装饰品);四品服绯,金带十一銙;五品服淡绯,金带十铐;六品服深绿,七品服浅绿,皆银带九铐;八品深青,九品浅青,皆输石八銙(孔雀石);未入流的小官及庶人,服黄衣,铜铁带(钅夸)七枚。
又士子穿裥衫,庶人衣白。方外则缁衣黄冠。
因为无品级老百姓等人穿黄穿白,唐人传奇中侠士有黄衫客。唐与高丽安市之战中,太宗与许敬宗登高观战,见一人穿白衣、持双戟,所向无前,召见之,乃薛仁贵。
又肃宗与李泌并马循行营垒,远远望见的人说:“黄衣者圣人,白衣者山人。 ” 又唐代用鱼符,群臣出入宫门以为验证,其后改为龟符,继又改为鱼符。
三品以上佩金鱼、金龟,四品用银龟或银鱼,五品用铜龟、铜鱼。所以李商隐《为有》诗:“无端嫁得金龟婿,辜负香衾事早朝。”
白居易《脱刺史绯》诗:“无那娇痴三岁女,绕腰啼哭索银鱼。 ”罗振玉《历代符牌图录》中尚收有唐代铜鱼、铜龟实物。
妇女的服装,皇后妃嫔皆有自己的章服,详于新旧《唐书》车服志、舆服志。命妇的法服是“翟衣”。
翟,就是雉鸡(长尾的野鸡),以青的衣裳,将翟毛编绣于上,故名“翟衣”。按九品分为九等,是正规的法服。
其次是“钗钿礼衣”,以所贴花钿多少分等级。一品夫人九钿,二品八钿、三品七钿、四品六钿、五品五铀。
六品以下直至九品官妻,则穿大袖连裳。妇女的便服,与其夫同色。
杜甫《丽人行》:“绣罗衣裳照暮春,蹙金孔雀银麒麟。”又说:“珠压腰(衤及)稳称身。”
腰(衤及)是妇女的内裙,日本妇女的和服仍因之,名为“腰(扌卷)”(koshimaki)。 可见平日妇女的盛妆,也不拘于法定的衣裳。
妇女的发髻,在沿袭古式上,推陈出新,不拘一格。但看传世周昉画的《仕女图》的发式,和日本已婚妇女所梳的“丸●”(mazu-mazuge)完全一样,可能是最流行的基本发式,所以被日本吸收保存至今。
另有名为“屏笙”的宫妆,式已不传,顾名思义,可能是一种高髻。饰品钗钿钏弭类,还有一种“步摇”。
戴在头髻上,走起路来颤颤地摇动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所说:“云鬓花颜金步摇”,即是。
春天还用纸折为方形或旙样物饰在头上,名为“方胜”,又名“春胜”。妇女的红妆,弄粉调脂、画眉、点唇和贴花钿外,还有“梅妆”。
据说是寿阳公主醉卧在梅花下,梅花落于额上,遂制此妆。唐代妇女尚未缠足,着展,见周昉《仕女图》。
4.唐宋女子服饰用语
服饰逐渐的开放,强调体态的美感,配挂披或胡帽;鞋子除云头高履外还出现了小蛮靴。
在加上织品的发展,许多轻薄细柔的布料被开发出来,因此透明的、多层次的穿着开始引领风骚。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装特色有:袒胸、高腰、披巾、明衣、男装、胡服和所谓的“时世装”等。
唐代仕女下装多穿裙子,腰束的极高,甚至高过胸部。裙色以红、紫、黄、绿最多,其中以红色最为流行。
衣身袒胸短襦、肩披宽长的肩巾、下穿高头云履。妇女服饰展现性感魅力,其中著名的是明衣的使用。
明衣原属礼服的中单,是用透明的薄纱制成。在以往只当作内衣穿着,但是在盛唐时期,明衣被拿来当作外衣,并成为盛装。
唐朝女装有汉族的襦裙装、女着男装和着胡服三种。 一,襦裙装。
襦裙装为唐代女装主流,其风格又随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发展有很大改变。初唐之时,襦袖皆窄短,群亦修长紧裁,基本适应建国之初国力并不十分强盛,需要节俭适度的现状。
到盛唐之时,女装的裙子向宽大、飘扬之势发展,诗人描绘到,裙裾甚至可拖六湘水,可拂扫落梅。(“ 裙拖六幅湘江水”李群玉《 同郑相并歌妓小饮戏赠》、坐时衣带萦纤草, 行即裙裾扫落梅”孟浩然《春情》)此时女性美已如牡丹般豪华富贵,有登仙情怀。
盛唐之时流行著名的唐“袒胸装”,即以薄透纱罗掩胸前,腰线抬高至胸下或直接束在胸前,不着内衣,上衣对襟,袖子极其宽阔肥大奢华,并在肩披有繁盛纹饰的帔帛。从贵族官僚士大夫家妇人,到歌舞妓女,以至普通百姓人家的女子,甚至连女道士,都有着袒胸装的情况。
唐诗中赞颂袒胸装的佳句甚多,如方干《赠美人》:“粉胸半掩凝晴雪”周濆《逢临女》:“慢束罗裙半露胸。”这种衣袂飘舞和裙带当风,是盛唐朝气蓬勃和高度物质文明的艺术释放,是在生活富足之上对美的追求,对自己的信心和对人性的赞颂。
而到了中晚唐,服饰在原来风格的基础上,更加奢靡与昏金暗玉,体现出一种心理上的低迷状态。安史之乱后,唐朝走到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,社会动荡民生不宁,贵族阶级更是庸碌无能,转向沉溺享乐。
服饰也转向了多元化和精细化。 二,女着男装。
天宝年间, 妇女皆以着男装为美,唐高宗时, 太平公主服武官装于宫中表演歌舞; 唐武宗时, 王才人与武宗装束同样, “……使得奏事者将男女混淆不清, 常常认错武宗却以此为乐。”“俄又露髻马驰俜, 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, 而尊卑内外, 斯一贯矣。”
“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,与丈夫无异”元稹诗《 赠刘春》云“: 新妆巧样画双蛾, 漫裹常州透额罗。正面偷匀光滑笏, 缓行轻踏破纹靴。”
女着男装是受了胡人风气的,同时也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和男性审美观念的转变,这种宽容尊重并包的姿态不仅体现在对女性上,还流露在对四方之国蛮夷之族的政策上。正如唐太宗说:“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。”
三,着胡服。开元年间,妇女常着胡服出行,以此为时尚。
胡服即领、袖、下摆处有绵边装饰,对襟、折领或圆领、窄袖,头戴高沿毡帽,束革带,有小饰物,下穿竖条小口裤,脚穿尖头绣花鞋、半靿软靴。《花蕊宫词》诗“明朝腊日宫家出, 随驾先须点内人。
回鹘衣装回鹘马, 就中偏称小腰身。”和《旧唐书舆服志》中记载:“开元初, 从驾宫人骑马者, 皆著胡帽, 靓妆露面, 无复障蔽。”
元稹《法曲》“自从胡骑起烟尘, 毛毳腥膻满咸洛。女为胡服学胡妆, 伎进胡音务胡乐。
火凤声沈多咽绝, 春莺啭罢长萧索。胡音胡骑与胡妆, 五十年来竞纷泊。”
都形象地表达了胡风胡气对唐朝的影响之大之深。这种现象,与唐朝开放政策是关系紧密的。
同时社会安定,经济富庶,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自信所以敢于开放,乐于对外交流,吸纳和融合,而自身始终是坚定的,昂扬的,王者之花怒放着的。 在服装的样式之外,衣裙的色彩装饰和容貌的妆容发型也是服饰的重要一面,是更加绽放光彩的一面。
唐代服饰的刺绣文饰是精密奢华的,仙花瑞草珍禽珑兽吉祥图案无所不包,绚烂多彩喷薄夺目。唐代女子喜欢红、浅红、淡赭、浅绿等明艳的色彩,并加以金银彩锈为饰,尤其喜欢石榴红裙。
石榴红裙也多出现在诗词作品中,如,《琵琶行》:“血色罗裙翻酒污。”万楚《五日观妓》:“眉黛夺得萱草色,红裙妒杀石榴花。”
一个喜好红色的时代,必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激昂的时代,是个富贵的张扬的年代。唐代女子发式多变,常见有半翻、盘恒、惊鹄、抛家、椎、螺等近三十种,上面遍插金钗玉饰、鲜花和酷似真花的绢花。
唐朝的化妆样式也种类繁多,新花样新流行层出不穷。《唐国史补》中记载:“天宝之风尚党,大历之风尚浮,贞元之风尚荡,元和之风尚怪。”
浓妆艳抹,色彩艳丽是总体的风格,甚至经常会出现追求怪异奇特的妆容,是物质生活过于富足百无聊赖的一个侧面。
5.关于形容古代女子衣着很美的诗句
“其形也,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,荣曜秋菊,华茂春松。
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,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,皎若太阳升朝霞;迫而察之,灼若芙蕖出渌波。
秾纤得衷,修短合度,肩若削成,腰如约素。延颈秀项,皓质呈露,芳泽无加,铅华弗御。
云髻峨峨,修眉联娟,丹唇外朗,皓齿内鲜。明眸善睐,靥辅承权,瑰姿艳逸,仪静体闲。
柔情绰态,媚于语言。奇服旷世,骨象应图。
披罗衣之璀粲兮,珥瑶碧之华琚。戴金翠之首饰,缀明珠以耀躯。
践远游之文履,曳雾绡之轻裾,微幽兰之芳蔼兮,步踟蹰于山隅。于是忽焉纵体,以遨以嬉。
左倚采旄,右荫桂旗。攘皓腕于神浒兮,采湍濑之玄芝。
6.古代衣服描写
1、淡粉色华衣裹身,外披白色纱衣,露出线条优美的颈项和清晰可见的锁骨,裙幅褶褶如雪月光华流动轻泻于地,挽迤三尺有余,使得步态愈加雍容柔美,三千青丝用发带束起,头插蝴蝶钗,一缕青丝垂在胸前,薄施粉黛,只增颜色,双颊边若隐若现的红扉感营造出一种纯肌如花瓣般的娇嫩可爱,整个人好似随风纷飞的蝴蝶,又似清灵透彻的冰雪。
2、碧绿的翠烟衫,散花水雾绿草百褶裙,身披翠水薄烟纱,肩若削成腰若约素,肌若凝脂气若幽兰。娇媚无骨入艳三分。
3、葱指上戴着寒玉所致的护甲,镶嵌着几颗鸽血红宝石,雕刻成曼珠沙华的形状,美丽不可方物。绝美的脸映在铜镜中,并没有老去的迹象,仍然十足的娇艳。
一头长发被侍女憟嫣挽起,用象牙雕花的梳子梳成松松的飞星逐月髻,插上了两支赤金掐丝暖玉火凤含珠。
7.唐朝服饰的介绍(急需大量文字介绍,特别是关于女子服饰的)
初唐文吏服饰 唐代文吏服饰 唐代官吏,除穿圆领窄袖袍衫外,在一些重要场合,如祭祀典礼仍穿礼服。
礼服的样式,多承袭隋朝旧制:头戴介帻或笼冠,身穿对襟大袖衫,下佩围裳,玉佩组绶一应俱全。在大袖衫外加着裲裆,也是隋唐时期官吏服饰的一个特点。
从出土的陶俑、壁画来看,穿着这种服饰的官员,身份不会太高。本图为戴介帻、穿大袖衫的初唐文吏。
(彩绘陶俑,传世实物,原件现在藏上海博物馆)。 唐代大袖衫及裲裆 唐代文吏服饰--唐代官吏,除穿圆领窄袖袍衫外,在一些重要场合,如祭祀典礼仍穿礼服。
礼服的样式,多承袭隋朝旧制:头戴介帻或笼冠,身穿对襟大袖衫,下佩围裳,玉佩组绶一应俱全。在大袖衫外加着裲裆,也是隋唐时期官吏服饰的一个特点。
本图为戴冠、穿大袖衫及裲裆的文吏(河南洛阳关林出土唐三彩俑)。唐代文官大袖礼服 唐代文吏服饰--唐代官吏,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,在一些重要场合,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。
礼服的样式,多承袭隋朝旧制,头戴介帻或笼冠,身穿对襟大袖衫,下着围裳,玉佩组绶等。本图为唐代文官大袖礼服展示图(根据出土陶俑及壁画复原绘制)。
唐代文吏冠饰 唐代文吏服饰 唐代冠帽有幞头(由起初一块包头布逐渐演变成有固定的帽身骨架和展脚的完美造型)、进贤官(为历史上重要的冠式,在唐宋法服中仍保持重要地位)、平巾帻及武弁(平帻巾与武弁是同一种冠式,是古时一般人裹在头上的布,后成为只能罩住发髻的小冠,即平巾帻)、笼冠及貂蝉(将貂尾插在平帻巾上,平帻巾外罩笼冠)、武士冠(在帻上戴一种雄鸡冠)、通天冠及进德冠(通天冠是级位最高的冠帽,与进贤冠结构相同,不同的是展筒的前壁)等等。本图左1、2、3为戴武士冠、平巾帻、武弁的文吏(长安城郊隋唐墓出土陶俑)。
右1为戴武弁的文吏(河南洛阳出土陶俑)。唐代文吏服饰 唐代文吏服饰 裹幞头、穿圆领袍衫是唐代男子的普遍服饰,以幞头袍衫为尚。
幞头又称袱头,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。唐代以后,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,名为“巾子”。
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。除巾子外,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,到了晚唐五代,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。
唐代官吏,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,其颜色曾有规定:凡三品以上官员一律用紫色;五品以上,绯为色;六品、七品为绿色;八品、九[品为青色。以后稍有变更。
另在袍下施一道横襕,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。此土为裹幞头、穿圆领袍衫、乌皮靴的官吏(陕西乾县李重润墓壁画)。
唐代官吏常服袍衫之一 唐代官吏服饰 唐代男子服饰,以幞头袍衫为尚,幞头又称袱头,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。唐代以后,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,名为“巾子”。
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。除巾子外,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,到了晚唐五代,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。
唐代官吏,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,其颜色曾有规定:凡三品以上官员一律用紫色;五品以上,绯为色;六品、七品为绿色;八品、九[品为青色。以后稍有变更。
另在袍下施一道横襕,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。此土为裹幞头、穿圆领袍衫的官吏(唐人《游骑图卷》局部)。
唐代官吏常服袍衫之二 唐代官吏服饰 唐代男子服饰,以幞头袍衫为尚,幞头又称袱头,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。唐代以后,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,名为“巾子”。
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。除巾子外,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,到了晚唐五代,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。
唐代官吏,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,其颜色曾有规定:凡三品以上官员一律用紫色;五品以上,绯为色;六品、七品为绿色;八品、九[品为青色。以后稍有变更。
另在袍下施一道横襕,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。此土为唐代圆领袍衫展示图及纱罗幞头图。
唐代官吏常服 裹幞头、穿圆领袍衫的帝王及官吏(阎立本的《步辇图》)。《步辇图》画的是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,吐番丞相禄东赞前往京都长安,迎文成公主入藏,受到唐太宗接见的历史故事。
画面右侧坐在步辇上的是唐太宗。左侧站立三人,中间一人戴毡帽、穿锦袍的是吐番使者丞相禄东赞。
另外两人都是唐代官吏。唐代男子服饰,以幞头袍衫为主,在这幅作品中反映得比较全面。
画中男子除吐番使者外,都着幞头袍衫,连皇帝也不例外。按照常规,皇帝接见宾客,应穿繁重的礼服,而本图所绘通穿常服,这既表现了汉藏两族的亲密无间,也反映了幞头袍衫在当时流行的程度。
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 《礼宾图》 图上左面三位为唐朝 鸿胪寺 官员,相当于现在的外 交部。章怀太子李贤生活在西历7世纪后半业,唐朝中前期袴褶服曾作为上朝之用,但是日常上朝所穿的衣服并不是所谓“朝服”。
也叫具服,但是下面为白裙,而不是袴。唐代妇女服饰 穿大袖纱罗衫、长裙、披帛的贵妇(《簪花仕女图》局部)。
大袖衫裙样式为大袖、对襟,佩以长裙、披帛。《簪花仕女图》描绘的是贵族妇女在庭院中散步、采花、捉蝶及戏犬时的情景。
图中人物服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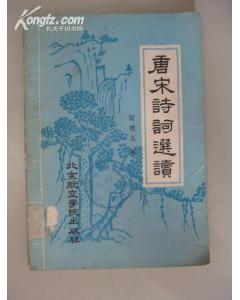
声明:本网站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,根据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,如果我们转载的作品侵犯了您的权利,请在一个月内通知我们,我们会及时删除。
蜀ICP备2020033479号-4 Copyright © 2016 学习鸟. 页面生成时间:3.368秒









